魏晉之後,王弼版【道德經】以及他的【道德真經註】超過河上公,成為歷代解老註老者的案頭必備,盡管帛書,楚簡本【老子】出土,依然不能蓋過他的風頭。
當代解讀【道德經】的重鎮陳鼓應、樓宇烈、南懷瑾等等,經常參照王註,但多跳出王弼註原意,樓宇烈即使對「王弼註」進行校釋,依然屬於「另起爐竈」,支離破碎不得要領。

本文以「太上(第17)章」為例,分析探討他們在理解老子思想上的差異,同時反觀我們的理解偏差。
原文:「太上,下知有之;其次,親譽之;其次畏之;其下侮之;信不足焉,案有不信。猶呵,其貴言也。成功遂事,而百姓謂我自然。」
這一章有四個問題需要比較和探討:
1:「太上」是「最好的世代」?還是「最好的君主」?
2、「信不足焉,安有不信」,是「誠信不足」,還是對「道」的信心不足?「安(焉)」字到底是什麽意思?
3、是「 猶 呵,其貴言」?還是「 悠 兮其貴言」?為何「悠」字最易誤解?
4、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,其中的「我」是百姓的自稱,還是百姓對聖人的他稱?

「太上」是「最好的世代」?還是「最好的君主」?
王弼註解「太上,下知有之」說:「太上,謂大人也。大人在上,故曰‘太上’也」,「大人在上,居無為之事,行不言之教,萬物作焉而不為始,故不知有之而已」。
河上公雖然將「太上」理解為「太古無名之君」,與下文文義略顯不恰,但跟王弼一樣,都是把「太上」理解為君主。
古代註釋【道德經】的,隨機抽取10人,巧了,無論把「太上」理解為「大人」,還是「聖人」,或者「君子」,但都是「人」而不是「時代」。
陳鼓應、南懷瑾則分別把「太上」理解為「最好的時代」和「形而上的道」,南懷瑾的解說更奇特:形而上的道,卻是那些看起來最愚蠢的人才知「道」。
按照陳鼓應的邏輯,「太上,下知有之」,就應該是「最好的時代,人民只是感覺到‘最好的時代’的存在」。如此理解,邏輯不通。
樓宇烈對王弼註的「校釋」反而違背了王弼原意,他說:「太上,是指偉大的領袖……這是以崇尚最上層次的道德規律來統治」。
樓宇烈把最好的道治模式直接當作退而求其次的「德治」「仁治」來理解了,混淆了「無為」與「有為」的關系。並且「道德規律」乃是生造詞匯,與道治毫無關系。

比較分析:
「太上」只能指向「大人」「君王」等具體管理者,這樣才能跟「知之、親譽之、畏之、汙之」相匹,從「太上,下知有之;其次,親譽之;其次畏之;其下侮之」的表意來看,這是老子對統治者從「道治」到「德治」「仁治」「智治」漸次下滑過程的社會現狀描述。
在有道社會,百姓知道有一個聖人一樣的管理者,因為他「無為」,不強力幹涉百姓的自由生活,所以百姓只會偶有提及,既不覺得親近,也不覺得反感,就如同一個自然物的存在。
但接下來的君王就不同了,他們是「有為」的,是「大道廢,有仁義」的表現,他們施行仁政德治,因此百姓親近並贊譽他。再次一等的君王,「以兵強於天下」,以暴政虐民,以殺伐立威,強迫百姓就範,侵奪百姓利益,百姓怕他卻敢怒不敢言。
最下等的君王就是昏君了,他昏聵不明、荒淫無道,卻會跟百姓耍小聰明,與百姓離心離德(王弼大意),已經到了天怨人怒的程度,所以天下人都在貶斥他,侮辱他,跟他水火難容了。
所以,陳鼓應把「太上」理解為「最好的世代」是不對的。樓宇烈對「王弼註」的白話文轉譯,更是肢解了王弼註的原意,且邏輯混亂,語法不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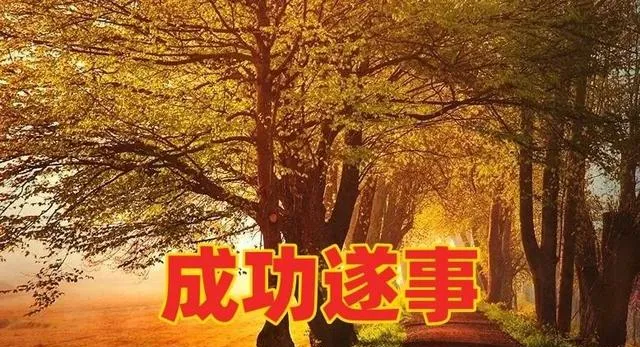
「信不足焉,安有不信」,是「誠信不足」,還是對「道」的信心不足?
這個 問題還涉及到「安(焉)」字到底如何解釋的問題。
按照陳鼓應的解釋,其意是:統治者的誠信不足,人民自然不相信他。南懷瑾則認為天生智慧有分級,就像佛教所說的「根器」不同一樣,人們對「道」的理解程度也不同。他的理解雖然有所偏差,但他畢竟還是避開了誠信之說,而認為是「信不通道」的問題。
還是王弼、李榮、蘇轍等人的理解更好。
王弼說「輔物失真,則疵釁作。信不足焉,則有不信,此自然之道也。已處不足,非智之所濟也」。
就是說:道輔佐萬物,順遂物性而不失其真,就不會出現波折。若通道不堅,半信半疑,則假借仁義智巧之術彌補之,結果適得其反。
蘇轍【老子解】說:「吾誠自信,則以道禦天下足矣。唯不自信,而加以仁義,重以刑政,而民始不信矣」——君王自己對大道都不自信,只好假借仁義,輔以刑罰,導致百姓跟著懷疑大道的存在與作用

樓宇烈在校釋王弼註時說:人若失信,別人也會對他失信,這是自然規律。已經處於不足、被動的地位,不是智力能夠扭轉局勢的。
他把王弼理解的「自然之道」理解為自然規律,把自己道心不足,理解為「出於不足、被動地位」,實屬曲解。而「不是智力能夠扭轉局勢的」的說法,更是不知所雲。
所以,「信不足 焉,案有不信」根本不涉及上下之間的誠信和信不信任的問題,而是關於信不信「道」的問題。即君主都對大道「信不足矣」,況乎天下人?
順便說一下「安有不信」中的「安」,傳本寫作「信不足焉,有不信焉」,但楚簡本和帛書本皆是「安有不信」,很多人望文生義,以為反問句:「怎麽會有不信」?其實不然。
這個「安」不是疑問詞,而是連詞,作「乃」「於是」使用。老子說「執大象天下往,往而不害安平泰」,荀子說:「委然成文,以示之天下,而暴國安自化矣」,其中的「安」都作「於是」、「則」、「乃」字用。

「猶呵,其貴言」與「悠兮其貴言」,一字之差謬之千裏
傳世本【道德經】諸版本,以及出土的帛書本、漢簡本、楚簡本諸本全是「猶兮其貴言」,唯有王弼本是「悠兮其貴言」。「猶」與「悠」一字之差,帶來諸多理解障礙。
「悠」雖有憂思之意,但人們多把它理解為是悠然、閑適、安閑、從容不迫之意,理解為陶淵明所說的「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」之意,所以王弼本雖然「悠兮,其貴言」含有謹慎之意,但後人不解其意,都把悠理解為「悠然」,比如陳鼓應就是這麽理解的。
老子描述聖人、「古之善為道者」,其基本特征都是謹慎,不輕言、不任性,所有用「猶」字更能跟「貴言」——不輕「言」聯系起來。
所以,「猶呵,其貴言」指的是為道者謹慎從事,「若冬涉水」、「若畏四鄰」,因為政令繁苛,會「帶來「天下多忌諱」,民怨由此滋起,導致「百姓之不治」。
所以,河上公解釋說:「太上之君,舉事猶,貴重於言,恐離道失自然也。」

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,其中的「我」是百姓的自稱,還是百姓對聖人的他稱?
這是一個爭議持久而普遍的老話題,本人也曾堅信「我自然」是百姓的自稱,但後來接受了劉笑敢先生的大觀點,他對此做了大量考證,認為「我自然」,是百姓對聖人「猶呵,其貴言,成功遂事」的評價。
很多人從字面上來看,認為這是老子對權力實行道治後,百姓對自身無拘無束、自由自在生活狀態的由衷稱道。
因此,像河上公、成玄英、蘇轍、憨山德清等等那樣的大家,也都認為是百姓的自我評價,比如河上公說:百姓「反以為己自當然也」。憨山德清說:「人人功成事遂,而皆曰我自然耶。」陳鼓應說:百姓都說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。
果真如此嗎?如果不是聖人「以道蒞天下」,如果百姓「重死而遠徙」,還能說他們本來的狀態就是那那樣的嗎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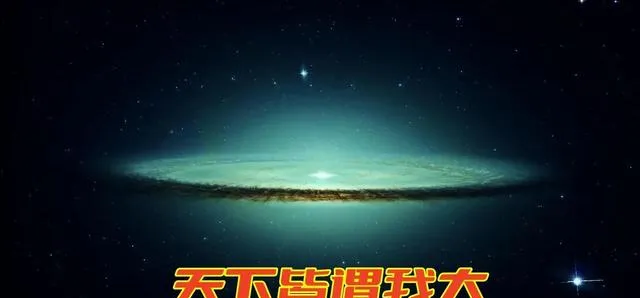
前文既然說「信不足有不信」,很顯然,百姓信不通道,取決於聖人行不行道,而「猶呵,其貴言也,成功遂事」正是對聖人為道的描述,因此「百姓謂我自然」,是百姓對聖人無為不幹涉百姓生活的評價。
歷代名家對「太上」的理解,基本上都是「大人、聖人、太古無名之君」,我所隨機查閱的「註老」大家,從河上公、王弼、成玄英、李榮、蘇轍、林希逸,到黃元吉、南懷瑾,包括唐玄宗、宋徽宗、明太祖等「禦註」,無一例外。
而「猶呵」「貴言」「成功遂事」更是聖人的「無為」特征,因此「成功遂事,而百姓謂我自然」只能是對大道 「弗為而成」的說明,只能是對聖人的評價,而不是對自己貴言、成功的自我評價。
同時,「我」是大道和為道聖人的代稱,不是對萬物和百姓的指代,這大概是共識吧?
我們比較一下原文便知,【道德經】中前後出現17處「我」,全是對大道或聖人的代稱,如:我泊焉未兆,我獨遺,我愚人之心也,我無為,我好靜,天下皆謂我大,等等。
還有可參照的案例,比如67章「天下皆謂我大」,與「百姓謂我自然」句型句意一致,這個「我」明顯是特指道的。

劉笑敢的考證很詳細,簡言之就是:「謂」不是自言,而是對他人他物的評價。為道權力的使命在於無為,在於「輔」助百姓回歸「自然」,只有聖人「無為」不幹涉「百姓」,百姓才會評價他:他本來就應該是那個樣子。
百姓都想自由自在,無拘無束地發展創造,實作「自化」、「自富」。但是天上不會掉餡餅,百姓的「自然而然」不是天然地、自發存在的,它取決於權力是否「無為」,只有權力為道,才會有百姓的自由發展和自主創造。
只有當百姓獲得「自然」時,他們才會由衷地說:我們感覺不到他的存在。正如王弼所說:「大人在上,居無為之事,行不言之教,萬物作焉而不為始, 不知有之」,自然而已。
所以,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,應該是百姓對權力者「居無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」的稱道,而不是對自己的評價。











